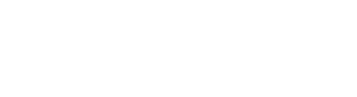一直以来,我对“左”和“右”的政治概念是相当模糊的。
简化的说法将左定义为进步主义,而右则是反进步的。在科技发展为世界带来福利的今天 ,这种定义下的左天然就有一种号召力,带领大家改变世界,引领下一个时代的到来。但有些时候,左又会被定义成激进主义,而又是保守主义。或者从政治上说,左是革命派,右是建制派。这种说法可能显得更加中立了一些,但建制派天然和“既得利益者”这个词联系到一起,因为只有获得利益了,才会去维护这个制度,从这一点说也是天经地义的。
在很多地方,左和右成为了复杂的维度。比如还是我们的教科书,比如Poliscale。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各有各自的左右尺度。经济上,全球主义会被认为是左派,贸易保护主义是右派。但是,特朗普上台之后,经济上的左右反而逆转了一样,中国至少在名义上成为了自由贸易的驱动者。文化上,左派传统支持女性、LGBT和黑人,右派似乎是白人和宗教主义。但现在相对于美国的运动,中国又成了梵蒂冈传统的支持者,民族主义的温床。是左右本身就是相对概念,还是我在左右的定义上还是模糊的呢?
我承认,作为一个在中部铁锈带居住过的普通学生,我对于政治和政治学术都不甚了解。聊天的时候接触大学生和本地人,看新闻从Fox News 到 Huff Post,也很难深入进去。只是印象里左派不太关注本地的乡下人,右派对于政治的热衷又低过橄榄球赛。这算是一种偏见吧。从萧瑟的Milwaukee开车出来,到热热闹闹的圣诞小镇,我很难不把自己和乡下民众联系起来,但在大学的时候,我又很难承认自己并不是十分进步。我花了很多时间思索这个问题。
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 给了我新的启示。按照介绍,这是一部左派视角的,倾听乡下民众的社会报告。这使我感到很分裂,以为可能又是左派对右派的一番羞辱,就像电视中的那些评论员每天所做的一样。后来我意识到是定义的问题。我认为,左派的进步性体现在对全社会理想的追求,右派的建制性则是在于对全社会现实的确认。左右不是相对的,也不是某一揽子被设定好的政策集,而是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两个不同方面,对全社会维护的理念。经济政策的摇摆并不意味着左右的转变,这样也能解释在先前的定义里文化为什么不总与政治相吻合。引用列宁的话来说,“近似于螺旋形的曲线”。
在这一报告中,乡下民众被作为一个新的个体对象被解释主义性地表达,通过对于他们的不满与怨恨调查,增进学界对于公众舆论这一概念本身的理解,以及对于整个公众决策制度的改进。作者关于调查方法和动因方面写得极其谨慎而详细。一方面是这种缺乏数据支持的谈话调查并不太受各种学界欢迎,这一点作为其他专业学生的我也是感触颇多;另一方面这种讨论最后很容易变成立场之争,对作者的学术前途可能也会造成影响。当然受访者对作者的态度也各有区别,但UW Mandison的纪念品大多数时候是有效的——尤其是确认这些纪念品并非来源于税金之后——和作者一样,不论左右,也不论乡下和城市,大家依然抱有着对本州乃至本国的热爱。
这种理解的尝试是极其可贵的。一直以来,许多政治理解认为,这些低收入人群(事实上按照城乡而非收入划分更加贴切)是受蒙蔽的对象,这些人是出于对民主党人/共和党人的怨恨而选择对方。在Wisconsin乃至全国的政治版图变化中,是民主党人/共和党人各自重新定位自我,而非选民发生了变化。这种根植于城市/乡村精神内部的身份、价值观和利益关系,才是进行选择的内生因素。或者至少是距离真实的更进一步。
在我的印象里,这种分歧比原本想象的更可怕。在极端化的今天,城市/乡村民众的认同差异不断扩大。是重拾孤立主义,还是继续拥抱全球化?是田园牧歌的美国,还是赛博朋克的美国?大家有无数的老问题和新问题需要解决,但最根源的,美国是什么?能够让大家摒弃左右的共识是什么?
这是急需解决的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