汤原麦金利
Tang Yuan McKinley
2
周围一片纯白,我跑在汤原一中的操场上,深一脚浅一脚的,大雪没过了我的脚踝。月光明亮,浅金色的轮廓下,远方隐约是麦金利雪山。
我本以为,汤原这么一个充满温泉气息的名字,总是要比林雪平要温暖一些。没想到还是被冷空气上了一课。身上的羽绒服是火车转大客时在佳木斯地下商城买的,老毛子标签。我在路上呼哧呼哧地喘着白气,它也斯哈斯哈地吐着羽毛。
枪托和扳机逐渐黏在手指上,从刺痛变成轻微的瘙痒。我抱着一大摞课本,小心地把枪从右手换到左手,有时再从左手换到右手。周围很安静,只有路灯的电流声。是散发着微热的白炽灯,令人喜欢。
–
当时我还在课桌前瘫着,盯着前桌女生的油头。因为要回家吃饭,所以在晚自习前的休息间隔走回去再走回来。每周还有一天要从楼下搬大桶水上五楼。只有这么几个男生,太累了,灯光晃眼睛。
本地的人还不错。虽然听说今年夏天实验中学在校门口砍死了两个,但总归是不错的。我把滑盖手机借给他们玩黑白棋,他们也拉上我一块打乒乓球。这对于转学生来说已经是极大的帮助了。在新雄安上高二的时候,因为不记得生物实验室在哪里,住校的我还是有一节旷课记录。匪夷所思,灯光晃眼睛。
来自过道的阴影冲淡了灯光,地理老师微笑着向我招了招手,然后坐在了黑板旁边的副主席位置上。
跳过碰撞的书包阵列,我和两个大盖帽徽章军大衣在阴影里。“我们是汤原人民内务部队,”他们的面貌难以辨别,但是似乎是我被安排在这里的原因,“她在哪里?”
“快,我们是来帮你的。”
–
路上有无数双眼睛在看着我。不知道是魂魄,还是半仙。似乎每个做点好事的人,死后都能变点什么。但是仙家又不总是干好事的,也许他们在第二人生里想换一种生活方式呢?动物就反过来,狐狸会偷鸡吃,但是狐仙就能保佑丰收。似乎动物对世界的态度更积极一点。
前一阵上学路上碰到了一条狐狸应该是讨封,精瘦精瘦的,上来就跟我讲上帝的旨意。我说你个入狐仙庙的怎么讲起圣经了,它说南边教堂发的盼盼法式小面包更好吃点,我信它了。
那狐狸现在就在月亮下扭腰,可能是我看错了。
–
我不知道该相信谁,地理老师乐乐呵呵地给我指了一条路。操场斜角那块的土地凹了一块,下雪看不太出来,春秋的时候好多小子从那逃课。
从雪坑里刨书的时候,我才想明白,刚才的两位朋友好像真是好人。
那地理老师图什么呢?可能他是觉得这玩意真有意思吧,找乐子是吧。
或者数十年如一日的,每天上课之前向同学推销二道街的地锅溜达鸡好吃,这会终于看见自己培养了几天的学生也溜达出去了。
–
我想梳脏辫,配上五颜六色的发饰,现在是中学男生统一的冲天炮短发,看着像三角形一样,所以何沐城管我叫麦金利。
为了不剪头发我还和教导主任吵了一大架,嗓子哑了,以至于即便是十几年后,每到春天我都咳嗽一场。也有可能是岛屿气候的花粉过敏。
那时候我还叫汤原麦金利,改的真名。他也叫汤原麦金利,改的笔名。
之后的汤原麦金利们什么都没写,什么都写不下去。他们把笔换成了无尽的生命,无数的生命,然后还不够秤,又添了一座北京城,二斤猪棒骨。
猪棒骨里没吸出来骨髓,一点都不多换,可真抠啊。
–
虽然家里可能已经不再安全,但我已经无处可去。不知道过了多久,我想着一切结束之后,如果真的也像他们一样参加高考,我大概会从汤原骑个自行车去北京,中间坐轮渡跨海的时候也骑,从头骑到尾,大概就是目前经过的时间。没有蒙蒙亮的天空,没有萤火虫般温暖的路灯,没有刚果平原,没有大众汽车,也没有家里的电波信号。
就此销毁证据。在做出决定的时候,他们的热浪已经逼近了。
–
如果预算还剩下可怎么办啊,我问汤原麦金利。
“那要不然再添个麦金利山吧,把它名字改成大秃顶子,这样就没人跟咱抢名字了。”
剧情里既然已经出现了手枪,那就一定有击发的时刻。
我把翻盖手机扔到面前的课本堆中间,用尽最后的力气打空弹匣。
四周的部队劈里啪啦的,佳木斯汽车站前的手枪地摊也劈里啪啦的,学校的蘑菇云也轰隆轰隆的。
–
“噼啪砰!”前桌的女生看着我,像魔法一样,从桌洞里掏出一罐啤酒,配着音打开了拉环。
(基于2019年10月/2020年6月《汤原麦金利》的原稿和2020年6月何沐城的《汤原麦金利(1)》,在原稿无法完成的条件下初步扩充大纲。希望在很久的以后能够完成它。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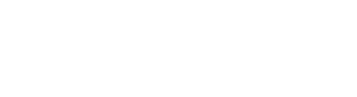
时隔四年再次更新的系列,就像在看卡在中间的老式幻灯片,一转一摇宛如白马过隙,一来一回早已物是人非,希望青梅姐姐永远年轻
谢谢你。